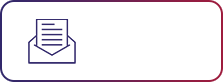我们这群留学生 专访法国汉学家雅克·班巴诺
原文作者 Helen | 发布时间 2015-04-21 | 浏览次数 5411
分享到:
拿着奖学金读北大
事情是这样的,1958年,中国想往法国派留学生,但是当时两国还没有建交,于是中国政府率先发出邀请,邀请两名法国学生去中国留学,这样一来,也许法国也会相应地邀请中国学生。一年前,北京大学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之间就已经签订了这样一个互派留学生的协定。不过法国外交部不接这个茬儿,当时法国承认的还是国民党政府,而且外交部又是法国政府部门里最反共的。事实上,戴高乐在1964年决定和中国建交的时候,直接跳过了外交部,因为他早就知道外交部会坚决反对。最后,外交部的人是看了报纸才知道法国已经承认中国了(笑)。不过法国承认中国是有条件的,戴高乐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两名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法国公民,其中一位叫魏智(Henri Vetch)。这个人是书商,在北京开法语书店已经有年头了。他入狱是因为书店里的一名日本员工。据说这个日本人和一个意大利人在1949年策划刺杀毛泽东(1950年9月,日本人山口隆一和意大利人李安东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参与策划炮轰天安门城楼、刺杀党和国家领导人,1951年8月被执行枪决。在此之前,山口隆一是北京东交民巷法语书店中文部的编辑。书店老板魏智被认定为共犯,判处十年徒刑,1954年被驱逐出境。这里班巴诺先生可能记忆有误——采访者注)。这到底是真事还是莫须有的罪名呢,到现在也说不太清楚。
话说回来,法国外交部的路没有走通,中国政府转而向法国共产党求助,通过一个叫法中友好会(Amitiés Franco-chinoises)的法共官方组织,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应届毕业生里挑选留学生。其中成绩最好的三个人里只有我想去,所以就是我了。我在北大待了两年,从1958年到1960年,拿的是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具体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在北京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缺钱,不仅因为奖学金给得多,还因为我为外文出版社工作。虽然当时也有所谓的外国专家,外文出版社还是需要校对稿子的人手,正好我既懂中文,又在索邦大学修过文学。他们有时候会在晚上十点给我打电话:“雅克,杂志明天就要出版了,你能不能现在就过来,帮我们最后再审一篇稿子?”要知道,外文出版社每个月都要对外出版宣传刊物,各国语言都有,中国编辑自己写的外语稿子总是需要润色的。这份工作的稿酬很高,因为外文出版社把我当专家对待,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价格付我翻译费,我在北京买书的钱就是这么挣来的。有时候他们要我把一整本中文书翻成法语,那我就可以出手阔绰地请朋友们去全聚德大吃一顿了!(笑)
在北京住宿是免费的,我当时住在北大老校区,就是原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的校址。那里美极了,有花园,有湖,而且听说我住的那幢房子在燕京大学时代是女生宿舍(笑)。那时候在北京城里还能看见城墙,到处都是胡同,胡同里鸡和兔子窜来窜去,马路上还有驼队经过(笑)。你随便找一块路边的大石基坐下来,就可能坐在一件文物上。那时候,北京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可惜现在都没有了,不然北京一定会取代巴黎,成为最多游客光顾的城市。
我在北京的第一年主要就是学语言,每天上午都有中文课,是小班课,只有四五个学生。我记得一位意大利女学生,她的丈夫就是所谓的“外国专家”,是意大利共产党派到中国来工作的。
第二年,我运气太好了,成了吴晓铃的学生!吴晓铃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研究领域的大学者,我在巴黎的时候就听说过他。当时他在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已经不带学生了。况且就算他愿意带学生,我也不能直接从北大转到中科院。因为根据协议,只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学生才有可能去中科院读硕士。我不死心,还是给中科院写了一封信,希望吴晓铃能收我。中科院很为难,一方面法国和中国之间还没有签订类似的协定,但另一方面,我是第一个毛遂自荐的法国留学生,直接拒绝也不太好。所以院方找到吴晓铃,跟他说:“现在有这么一封学生来信,我们院里不方便回复,不过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给他回信。每周安排一个下午,你在家里给他上课,这天下午你不用来院里,我们心里有数的。”
就这样,每周三下午,我去吴晓铃家,他给我开小灶。那年闹饥荒,北京城里人也得饿肚子。我记得有一家特供外国人的商店,店面不设在路边,而是在二楼,地方很隐蔽,店里卖各种罐头食品和香烟。对,那年连香烟也很难买到。每星期三,我会提两大袋罐头食品去吴晓铃家,上完课再提两大袋书回家,都是他借给我的(笑)。
在我们这群留学生里,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尤其多,俄罗斯学生的人数最多,捷克的,阿尔巴尼亚的,还有一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或者说来自那些被认为是受西方国家压迫的国家,比如说埃及。这批埃及学生来中国留学是为了以后能进埃及外交部工作,他们对政治一点儿也不关心,经常翘课,在北京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还四处留情,惹出不少是非。有一次,所有外国学生都被学校教导处叫去谈话,原因就是一个埃及男学生和一位中国女生乱搞。只听见教导处的人愤怒地说:“某某学生‘强奸’女学生,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次‘强奸’!(笑)”最后这个埃及学生因为和中国姑娘谈恋爱被学校开除了。当时黑人学生也不少,而且是各种各样的黑人,其中一个和我是好朋友,我们都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读过书。中国同学都问他:“你为什么和法国人交朋友?非洲以前不是一直被法国殖民者剥削吗?(笑)”他们不知道,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而他却和其他非洲来的同学有本质区别:有一批非洲留学生真的是农村孩子,他们对读书丝毫不感兴趣,而且有一个真的企图强奸中国女孩儿,还喝醉了挑衅警察。虽然最后闹事的非洲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但是影响确实不好。从阶级成分论的角度来看,来自农村的苦孩子不应该是最优秀的吗?外国留学生里还有蒙古的、印度的、印度尼西亚的,意大利的、东德学生也有。除我以外的外国同学在北大读完一年语言以后,都选了大学和专业,和中国学生一起再读了一年,听说他们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笑),只有我是特例,我去吴晓铃家单独上课。
我发现北大图书馆管理员都特别博学,所以我一度想回巴黎当图书馆管理员(笑),最后还是回母校当老师。北大图书馆里有许多外文书,都是那些被中国驱逐出境的外国人留下来的,还有很多流散到市场上了。在东安市场有一家很大的二手书店,里面全都是宝贝!光是关于性学的外文书就不少,比如有卡夫-艾宾(Krafft-Ebing(1840-1902)德国心理学家,著有《性心理疾病》)的著作!有一次企鹅出版社的人来北京,带了好多书到王府井的外文店卖,其中就有奥威尔的《1984》,在有关部门反应过来之前,就全被识货的顾客悄悄地买走了(笑)。我还在北京淘到一本不可思议的书:作者是俄国沙皇的警察头子,书写于1917年革命爆发之前。书里讲的全是宫廷丑闻,谁和谁传出性丑闻,谁敲诈勒索了谁,关于革命党竟然一个字也没提(笑)!扯远了。
明白很多事儿
我的中国朋友分两批,一批住北京市区,一批住北大校园里。我和同住北大校园的中国同学相处的时候是会有小麻烦的。中国同学来寝室找我聊天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来敲门,他会很害怕,怕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来找我,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私交是不允许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必须通过官方渠道。好在我房间里有三个大衣橱,我自己只要用一个就够了,剩下两个正好用来藏人(笑)。我和住在市区的朋友来往一点儿问题也没有,比如翻译家朋友杨宪益、李健吾都住在市里。对了,插一句,我记得一次我们一群外国学生由导游带着去爬山,那位导游问我是哪国人。我说:“我是法国人。”然后你猜他说什么?“啊,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国度!”(笑)我当时就惊呆了,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导游,在遇到中国游客的时候,会说“啊,你们来自杜甫和李白的国度”。
我认识诗人冯至,他以前在德国读书,后来一直在北大西语系当系主任。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北大西语系的——一夜之间消失了。我就去找冯至问问情况。先是他家的保姆来开门,我跟她说了说意图,她就进屋汇报去了。一会儿冯至的太太下楼来见我:
“冯先生不能见你,我非常抱歉。”
“我来不是非要见他,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我明白,但是我什么都不能
告诉你。”
她还问我:“你在中国待多久了?”
“半年多了。”
“你在这半年时间里一定明白很多事儿了吧。”她最后这么对我说。
冯友兰家我去过,这个吃百家饭的人,他家的小别墅那叫一个奢华漂亮!四九年前他就是蒋介石的眼前红人。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接他回北京,而一般人只能坐火车。等共产党的军队进了北京城,冯友兰激动地说:“啊,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笑)最后的结果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倒没怎么样,真正有想法的人反而受到冲击,他们才是一心向往革命,只不过他们心中的革命不是这样的。当时整个气氛就是四个字,人心惶惶!你提防我,我提防你,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刚到北京不久,去见一位中国朋友,问他当下的局势如何,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我临走前,从书架里取下《1984》,对我说:“看完你就全明白了。”那种恐惧让我印象深刻,现在的人批评中国,几乎张口就来,太容易了!因为他们不再害怕,只要你不挑战底线。可当时完全不一样,今天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当时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小心谨慎。总之,在北京这两年的经历让我后来没有成为毛派。啊,说到这批法国毛派,真是逗!“文革”一开始,他们那叫一个欢呼雀跃,还到处与人为师。可是他们支持的“文革”完全是臆想出来的,一旦发现真实的“文革”和自己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批人说变脸就变脸,最后攻击“文革”最凶的也是他们。
尽管我在北京只待了两年,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人的变化:比如官员最初也和普通人一样,骑自行车上下班,不过没多久他们就发现,有专车接送更好。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官员一开始的确很亲民,可是当各种便利和好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人很难拒绝,这是人之常情。对了,我想起学校的外办主任——她丈夫应该是某部长——我记得她慷慨激昂地给我们介绍北大学生游行的事儿:“我们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台湾,活动非常成功……我们一共组织了多少多少学生去英国大使馆前游行。”我心想,当年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开战的时候,我也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后来游行队伍还和警察起冲突,闹得很厉害。虽然最后仗还是打了,但是真正的示威游行是什么样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这和组织春游不是一回事。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官员也有诚恳的一面:比如说,他们给我建了一个档案,我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档案里的内容,知道了他们对我的评价:“知识分子,典型的资产阶级,不可靠。”(笑)这可真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反倒是等我回到巴黎以后,法国的安全部门监视了我整整一年,唯恐我在中国被人收买了。其间我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后才有朋友告诉我,他也是通过多重朋友的关系间接了解到的。我在中国最坦荡了,谁都知道自己是不是被人监视,躲躲藏藏反而多此一举。1965年我随一个法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我想借这个机会问候一下吴晓铃,就从旅馆给他打电话:
“我刚到北京,想来看看您,不过我知道您很劳累……”
“没事没事,最近没有政治运动,你来我家吧,我们一起吃晚饭!”
说到政治运动,我觉得人们多少有点装模作样的意味。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刚下火车,第一天到北大,才到校门口就看到一个人低着头站在一张桌子上,下面围了一群学生对着他吼。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战前法国最黑暗的时期。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参与者似乎有点演戏的意思,无论是批斗的一方还是被批斗的一方。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总之完事了以后,大家就说说笑笑、各干各的去了,有某种剧终散场的感觉。
在课堂里没学到什么
说到演戏,我在北京看了梅兰芳的演出!梅兰芳年纪大了,除了一些重大的官方演出,他已经很少出来了。有一天我从报纸上得知梅兰芳又出来演了,就跑到戏院买票。果然,售票处前已经排起长队了。等排到我已经没票了,我自然是恬不知耻地强调自己是法国人,说自己多么喜爱中国传统戏剧,果不其然抢到了第四排最中间的好位置(笑)。当天演的是《穆桂英挂帅》,梅兰芳一亮相——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台下的观众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长达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梅兰芳只能静止不动,一直保持着亮相时的姿势。我离他很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松弛的眼皮和下巴,一看就知道台上站的是一位老先生,这让我很难受。等观众重新坐下来,梅兰芳才开始演。一眨眼工夫,台上的老先生就变成了妙龄少女,真是不可思议!
平时我最喜欢去天桥看民间艺人表演:唱地方戏的、摔跤的、说书的、演木偶戏的,各种各样的表演,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和茶馆。我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可比大学多得多,我最爱听天桥的说书先生讲三国,还学会了下围棋。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我每次去都看到他在那儿和人下棋,我和他下过一次,一刻钟的功夫他就赢了(笑)。一开始我还带我的外国朋友去天桥玩,直到有一天学校找我谈话:“你一个人去天桥转悠也就算了,我们都了解你,可是你还明目张胆地带那么多外国友人去就不对了,这让他们对中国印象不好。”现在天桥没了,真可惜。听说他们后来重新造了几家茶馆,故意弄成古色古香的样子,好招揽游客,算什么玩意儿。
说真的,在北京这两年,我在课堂里没学到什么东西,平常到处走走反而收货很大。我记得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人民公社,蛮有意思:当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北京城里什么吃的都没有,市场上唯一不凭票就能畅买的食品是一种蜜枣,死甜,甜得我根本咽不下去!听说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要和伊拉克搞好关系,才进口了一大堆伊拉克蜜枣。那时候,北京居民都饿得面黄肌瘦,和二战时期的巴黎人差不多。或许不了解情况的人会把搞大跃进的人当作浪费粮食的恶棍,可这场灾难不是美国西部片,不能简单粗暴地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祸根不是恶,是愚昧。参观公社那次,我记得某位领导在谷仓里给我们介绍公社大跃进的成果,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一边逗母鸡玩,突然听到同行的东德同学提问——他是学经济学的:
“您刚才在演讲的时候说,公社一共拥有两百万头牲口。那么您所说的‘牲口’具体指什么?”
“啊,‘牲口’当然就是指牛、羊、猪、鸡、鸡蛋、拖拉机……”
“什么,鸡蛋和拖拉机?”
“对啊,拖拉机的马力有多少,不就相当于有多少匹马吗?填表的时候,鸡蛋没法当作粮食来计算,只能写到‘牲口’这一栏里。”
饥荒不就是这么来的嘛。
我都翻译了啥
说到我自己,我学中文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文明非常久远,而且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文明。古埃及文明也很古老,但是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持久的。二是从现实考虑,1950年代那会儿,中国和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还非常少,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没想要以后当大学老师,而是想在北京开一家法国画廊,把法国艺术家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的艺术家介绍到法国。就在我读本科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形势似乎越来越不适合我开画廊了,所以我就转学中国古典文学了。
回法国以后,我都翻译了啥?有寒山的诗,还有闻一多的诗歌。1980年代,具体哪一年我不记得了,两位外文出版社的编辑来巴黎找我,不巧我那时候生病了,她们还是坚持要见我,我只好气乎乎地去了。一见面,我就对她们发起了攻击(笑),我知道自己很不厚道:
“是不是又要翻译鲁迅?!怎么没有人想到翻译闻一多呢!他才是二战前中国最棒的诗人!”
没想到她们回答:“您想翻译闻一多就翻译闻一多吧,我们负责出版!”
“那我可就随心所欲地翻啦!”
“给您四个月时间,您随意!”
外文出版社真的出版了我翻译的闻一多诗选,但是碰到一个麻烦:我选了一篇闻一多分析屈原《离骚》的文章。文章里说,其实《离骚》表达了同性之间的恋情。要知道屈原本是楚怀王的情人,了解这段背景之后,你再读《离骚》,就能体会出其中的深意。让我想想,我还翻译了《东周列国志》……对了,还有司马迁!沙畹(Chavannes,法国汉学家)只翻译了《史记》差不多一半的内容,而所有的传记都是我翻的!我还翻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小集子,还有很多,一时想不起来了。
访谈手记
下午两点半,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先生准时出现在“艺术家柜台”门口。这似乎是采访的最佳时间与地点——冬日的午后与巴黎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当年我就是在路易大帝中学上的高中,离这里没几步路。”他轻声细语,一副绅士派头。突然间,十几个刚下课的大学生涌了进来,瞬间把吸烟区的座位全部占满。他们打情骂俏、高声谈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班巴诺先生被一阵阵的烟味熏得直咳嗽,但他并没有受到干扰。“那人脑子明显不够用。”“这也忒逗了!”他越说越来劲,使用着与旁边的年轻人同样的口气。但此时的他已经八十岁了。
1959年,法国正经历着阿尔及利亚战争和第四共和国的瓦解,而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大跃进的亢奋之中。两个国家各忙各的,鲜有交集。虽然1955年萨特和波伏娃访华,并撰文盛赞中国革命,但在那个时期,“毛主义”还没有在欧洲盛行。1958年,班巴诺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中文系毕业。与后来的一批法国毛派知识分子不同,他学习中文并不是受到革命的感召,去中国留学也不是出于对革命的向往。从1958年到1960年,班巴诺在北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和戏剧。如果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的再次革命,是对资产阶级的彻底清算,如阿尔都塞所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重新安置”,那么班巴诺所见到的中国社会则处于这场大变革的前夜——还残存着上一个时代的“古典”气息。反过来,那时的中国似乎也接纳了这位“古典”气息犹存的法国人:他对中国既无虚情假意的赞誉,也没有言辞激烈的批判,他感受到的是一个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中国社会。
最近这一年多,以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为名义的文化活动应接不暇。然而,热烈的气氛背后似乎只剩下两国间直白的经济利益诉求:法国沦为了中国人的消费天堂。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名牌专卖店到卢浮宫地下的巨大展厅(近年来,诸多中国艺术团体与公司花重金租用法国卢浮宫地下的卡鲁塞勒(Carrousel)展厅办展。该展厅是卢浮宫旗下纯商业运营的展览场地)。中国人对法国的文化只是消费,而这种消费是为了炫耀和贴金。另一方面,法国人则把中国看作是挽救经济颓势的一种可能,急功近利地捕捉各种商业机遇。在这场土豪与落魄公子哥的交往中,谁也不比谁更诚恳。相比当下,法国人班巴诺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真诚,尽管在那个时候,两个国家还没有建交。
这一段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在班巴诺的讲述中显得极具活力——一个二十多岁的法国小伙与“年仅十周岁”的新中国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因此,在下面的访谈中,我们隐去了自己的提问,使其成为班巴诺先生流畅而完整的自述,尽可能地呈现这位八十岁老人身上的青春气息。
来源:南方周末
【免责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留学说无关。留学说对文中事实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分享到:
文章评论
文章推荐

最热文章
更多文章